【GET2025】何妨徐行:50次对话的教育镜像

11月18日下午,随着左希《何妨徐行:50次对话的教育镜像》的主题分享,GET2025教育科技大会落下帷幕,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是左希。芥末堆里一个讲故事的人。
今年GET会场外的空气,比去年更冷了一些。
过去一年,我对话了50多位个体。今年的采访,常常伴随着沉默。采访变得越来越难。有人不愿意说,有人不敢说,哪怕是自己的故事,也会模糊、回避。
与去年那些直言不讳、落落坦诚的声音不同,今年的教育人有一些开始畏缩、开始隐藏。语言的变化,不仅是表达方式的转变,它还是权力的呼吸频率,也是不安的自白。

这些故事,我无法完全还原。从里面,我听见了呐喊,愤怒,希望与失落。那是人,栖息在这片土地上,而不是别的什么。
浮华盛世,往往掩藏着个体的动荡。
01
我今年接触的第一个年轻人叫张天瑞,网名“游标卡尺”。他说这是个理工科谐音梗,“游标卡尺不孤独”。实际上,张天瑞很孤独。
他是疫情三年的毕业生,投过上千份简历。为了活下去,他写过小说,做过剪辑,摆过小摊,扮充气青蛙,还做过保安。2024年,他一路骑行,从济南到深圳,卖掉所有家当,进电子厂拧螺丝。
为什么本科毕业要进厂?因为能攒钱。填资料时,人事主管提醒他,写本科学历不容易被选中。张天瑞随手一划,改成小学。从早八点到晚八点,每天12小时,整月无休,到手6500元。
他会拍短视频记录自己的生活,把自己整成了苦难的观察者,而不是其间一部分。
一年下来,他存了5万块,刚好够一笔劳务输出的中介费。今年春天,张天瑞告诉我,如果体检和签证顺利,下半年他就可以出国做工。他想去更远的地方看看。我祝福他,也提醒他要注意分辨中介的真伪。
过去四个月,张天瑞从社交圈彻底消失。最后一组动态,是他转去了苏州的另一家电子厂。流水线的线长警告他,不许乱拍视频,不准乱写东西。他和我说过,他很好奇,好奇一个普通人,该如何塑造自己的一生。

教育,像一台磨粉机,把人打成互不黏连的原子,再用风,把它们吹散。
02
公共空间的萎缩导致了对私人空间的窥伺。
我开始对年轻人的生存状态感到好奇。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教育流水线上的“产品”。
我联系上了另一个年轻人,叫刘然。他向我提了两个要求:一是不露脸,二是发布前做审查,不能给外人递刀子。
刘然是一名英国硕士,目前租住在北三环一间二十平的小房间,靠捡纸壳、饮料罐过躺平生活。
刘然的手机里,记录着每次卖废品的账本:纸壳2.15公斤,2元;1升塑料瓶3个,0.3元;500毫升塑料瓶18个,0.9元;250毫升塑料瓶8个,0.2元。今日收入,3块4。
他试着自洽,也会不好意思的闪躲,会被亲戚朋友揶揄,会被翻垃圾箱的同行大爷呛声。
刘然说,他尝试过很多选项,但每个选项都会后悔。也许,根本没有什么选项。我们都在生计和自我关怀间折返、奔跑,摇摇晃晃寻一丝喘息。
读什么书,找什么工,活什么样的人生,这些自我选择的幻觉,是人们最普遍的被动。社会学里有个词,叫“流动性熵增”,说的是结构没崩,但个体的能量持续消耗,局部次序维持,整体更加无序。
我们已回不到原来的格局。有时候,人仿佛感到一条路走到了头,或一只密闭罐子里的空气已耗尽。所谓穷途,就是无解。
03
微风起来,四面都是灰土。
橘子留美学心理学,回国后做英语戏剧老师。去年,她失业,在家照顾休学的妹妹。
橘子的妹妹是一名“网瘾少女”。瞒着橘子,母亲把她送进了广州一家行为矫正学校。妹妹是被两个男人连拖带绑抬走的。
橘子知道,妹妹害的不是网瘾,而是中度抑郁症。在中国的一些家庭,这样的病,往往被认为是矫情,或归咎于“手机害的”。家丑不外扬。
她到处求救,拿着妹妹的病历去社区、妇联、派出所说明情况。那些部门在听到橘子快30岁,没有结婚,没有工作时,态度倨傲且轻视。“我的妹妹是抑郁症患者,她需要帮助”。这句话,没人当回事。
橘子说,妹妹之所以这样,一部分是性格原因,另一部分,来自家庭与学校。母亲是“包办型”人格,她给你选择,却强迫你选她设定的答案。妹妹读寄宿制学校。他们把学校变成监狱的样子,吃饭、洗漱、睡觉都有要求,人与人不可以有交集。
妹妹被送去的戒网瘾学校又进一步。宿舍有摄像头,窗户是带铁栏的,走廊24小时有人值班,厕所没有门锁,每晚睡前要搜身检查。学校里等级森严。师傅带新人,新人不能和别人说话,组长专门监督,班委负责体罚。
在中国,这样的“学校”,至少有1400所。
当一个社会将独立意志视为禁忌,它的体面有序,不过是精巧的枷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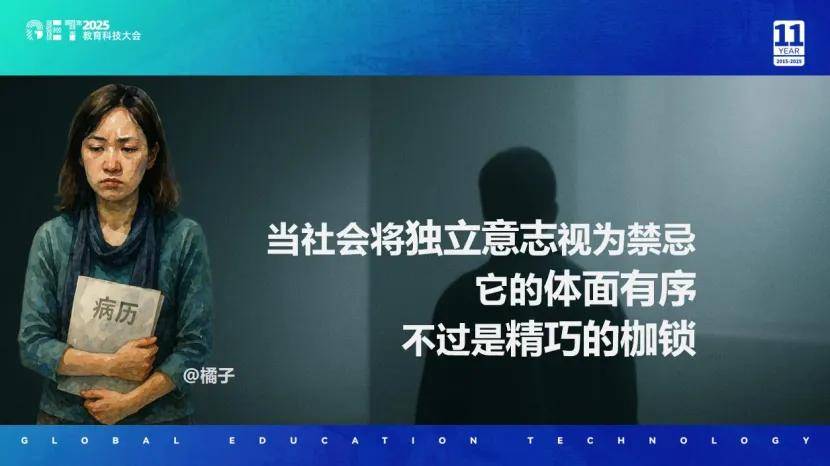
04
戴卫平的工作是在县城回收“烂尾娃”。
2025年,戴卫平心理咨询室接待的来访者越来越年轻,甚至有7岁的孩子,出现了明显的心理问题。
他一眼就能辨别来访者的病症。“抑郁的孩子最明显,眼神呆滞、空洞,注意力涣散。”很多孩子会在他面前崩溃大哭。
即便已经50岁,经历过无数次类似场景,戴卫平依然会感到失措。那些哭声,是撕裂内心的痛苦,仿佛一种深沉的绝望,在空气中涌动。
中国疾控中心曾发布《青少年心理健康地图》。25%的青少年有明显心理健康问题,青少年门诊人数在四年间翻了一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问题尤为突出,抑郁、孤独、焦虑、网络依赖,比一线城市的情况严峻得多。

未成年人的困境,从来不是他们一个人的事。他们会带着这些伤口长大,进入社会,累积成我们共同的未来。
在中国,持证的心理咨询师有180万人,但深入从业者不到15%。近九成的人,在短时间内选择离开了这个行业。即便如此,从业者几乎都集中在大城市。县城,成了这场心理风暴中被忽略的洼地。
性教育、爱的教育、死亡教育,本该关乎身体、灵魂与生命的意义。当这些教育缺席,人很难成长为真实、完整的人。青少年在其中一旦遭遇内心崩塌,他们能依靠的,往往是更沉重的规训和更漫长的自我修复。
05
很多时候,决定人一生的因素就是:生在何时、何地。时代和地域决定了个人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人如何了解世界,决定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36岁的张元,守护着两间图书馆,一间在台州三门,一间在嘉兴梅里。小镇的记忆藏在这两间图书馆里:房顶的水泥柱是村办工厂的遗物,马恩列的画像与儿童画并立,仓库被改造成阅读空间,偶尔夹杂着孩子的喧闹声。新与旧、记忆与现实,交织在这里。
张元不算帅,性格有些柔。从小被寄养在亲戚家,他说自己活得像个局外人。他为退役书籍举办破书展,给缺页的《小王子》画上星球,用毛线为散架的词典织封套;给阅览室的椅子穿旧网球做的鞋,发起书籍漂流运动,组织绘本剧、真人图书馆。图书馆的存在,不仅是架上的一排排书,更是一场场温柔而坚定的行动。
张元的图书馆里,安放着所有悬空的心灵。
37岁的潘丽云,拎着行李箱和孩子一起,回到了江西九江。十年的教培生涯,两次创业,三次转型,几乎赔光家底。
在这个不再许诺稳定的时代,成功变成了一种流动状态。人们在持续的流动中,寻找栖脚之地。短暂踌躇后,她拿起地图,挨个拜访省内的农场、庄园、营地,提供科学秀、魔法秀文旅演出,推半日营和周末营。两年赚了500万。
潘丽云说,现在的她是半年换一种活法。她变成了一个随时切换的角色,可以是项目经理、是演出经纪、是活动策划、是课程设计,什么都可以是。

在一个透明社会里,人们失去了模糊的权利,一切都要立刻回应,一切都须自证价值。
离北京2400公里外的云南镇雄,11月常常下雪。36岁的梁海荣在那里住了五年,他和团队的月收入是2000块。
镇雄曾是中国贫困人口比例最高的县,160万人口中,五分之一是留守儿童。梁海荣在那里做县域儿童阅读推广。从一间60平米,只有566册图书的阅览室开始,到3座公益图书馆,8所乡村图书室,56个村小阅读角,触达12000名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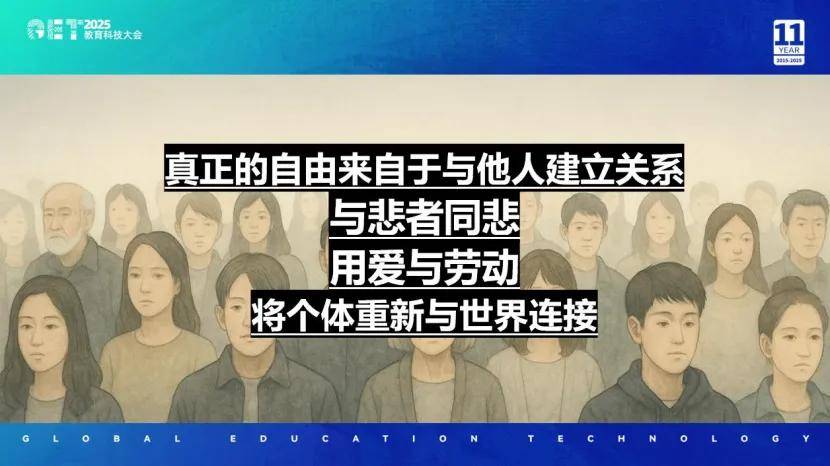
梁海荣自我怀疑过,大哭过,抑郁过,崩溃过。承载着三代人“教育能治愚”信念的梁海荣说,真正的自由来自于与他人建立关系,与悲者同悲,用爱与劳动将个体重新与世界连接。
06
以上是别人的故事,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我的爸爸是一名语文老师,大半辈子都在云南山区的边远学校里度过。他会大段大段地背诵鲁迅的文章。喝上一点酒,他会说自己是那个站着的穿长衫的人。
他会和我说:小囡,你也许没有权利去决定要做什么,但你至少可以在某个层面决定不做什么,不做什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阿瑟·米勒说,当一个时代基本幻觉疲惫的时候,可以说这个时代也就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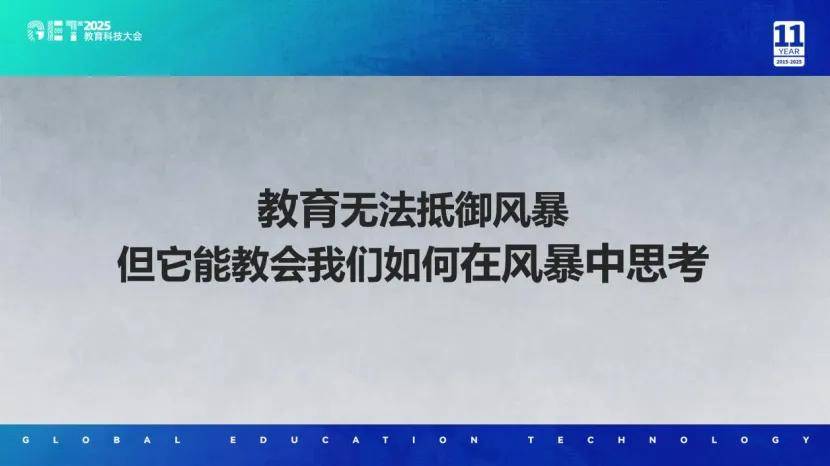
中国的教育培训行业正在经历一些变化,马太效应加剧,消费意愿下降,教育公平与社会责任成为企业核心命题。宏观向好,微观艰难,现实比报表复杂。教育无法抵御风暴,但它能教会我们如何在风暴中思考。
在创造性破坏的洪流中,教育人既是受害者,也是社会创新的引领者。教育,依然是被技术撕裂的时代中,唯一能让社会持续生长的机制。

然而,真正的增长来自内生创新,而非外部冲击。创新也不是引入新产品,而是打破旧结构。技术的引入,若不懂其为何有效,便毫无意义。
事实上,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是人的自由。没有自由,产业革命只是偶然事件,而非持续进步。
上个月,我和爸爸去了趟绍兴,去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我问他,对于未来,我们该乐观还是悲观?他和我说,小囡,这些争论,多是一群糊涂人的狂欢,乐观悲观没有高下之分,乐观的人可以基于虚妄的乐观,悲观的人也可以非常草率的悲观。
历史当然有不可测的偶然,但更有无可避免的必然。98年前,鲁迅在《野草》中写道: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
请大家多添衣服,保重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