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俞敏洪的南极信,给打工人制造了危险的“相对剥夺感”
俞敏洪又“翻车”了。
11月16日,正在南极“游玩”的俞敏洪发信祝贺新东方成立32周年。信中提到:“此刻,我正站在南极的冰雪世界中。四周是浩瀚的洁白、翡翠般的冰山和无边的宁静。冰川在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时间的力量与坚守的意义。”
接下来两天,他又连发了10条南极游视频。有媒体了解到,俞敏洪南极之行所乘坐的邮轮,一人入住的价格约为148万元(29天28晚)。
老俞可能本打算激励员工,最后却被“骂”上热搜:“老板缺乏共情”。
美国社会学家斯托福提出的“相对剥夺感”理论,解释了这种“员工在加班,老板在南极”的反差为什么会造成舆论反扑。
因为个体或群体与参照群体进行横向对比后,若感知处于劣势地位,将产生愤怒、不满等负面情绪。简单来说,“剥夺”是相对的,痛苦来自比较,不患寡而患不均。
精英叙事频频翻车只是表象,其本质是一种微妙的“相对剥夺感”正在蔓延,而这种“相对剥夺感”是危险的,它可能使“被剥夺者”丧失掉很多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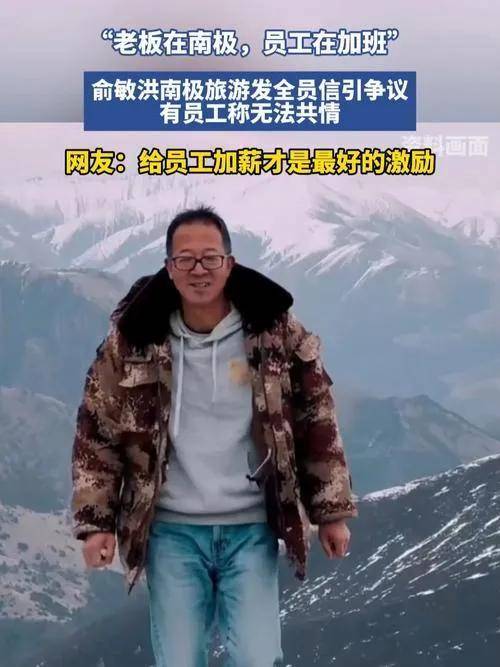
斯托福在半个世纪以前首次提出“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他在《美国士兵》一书中分析了二战期间士兵的心理和行为,发现美国空军士兵的晋升速度远比宪兵快,导致宪兵部队即使待遇不错依然士气低落,因为他们对比的是晋升更快的同龄人,而非普通民众。人们不会与遥远的标准比较,而是选择身边的参照物。
相似地,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也做过一个比喻:“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 这座小房子表明其居住者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可言;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服,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

俞敏洪的南极信之所以引发舆论不满,正是因为创造了这种“相对剥夺”的强烈对比:老板在南极享受诗和远方;员工在办公室加班处理眼前的苟且。落差感又进一步在社交媒体上发酵,引发更多“打工人”的情绪共振。
更为微妙的是,这种感受在经济下行期更容易被放大。因为经济高速增长时,水涨船高,大家忙着搞钱,无暇比较,甚至可能会憧憬“跟着这样的老板,我也能去看世界”,进而斗志昂扬。在钱不好赚的时候,人容易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变得更敏感、更易受刺激,这时俞敏洪的南极信就成了导火索。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提出需要警惕这种“相对剥夺感”蔓延:弱势群体成员经常体验到基本权利被剥夺的感觉,这种被剥夺感不仅使他们丧失掉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机会,还会对其心理发展带来损害。

其实,“相对剥夺感”对弱势群体是危险的。在二战士兵的案例中,宪兵因不满晋升机会远少于空军,而士气低落,更难争取到立功晋升。而且实际上,如果宪兵将自己的参照群体从“空军”改成“他们家乡那些留在煤矿工作的儿时伙伴”,那么他们的感受会截然不同。
在房子寓言中,一座很不错的房子因为靠近宫殿而相形见绌,居住者便倾向于在心理上自我矮化,在想象中把自己家构建成“茅草屋”,并编织出一套“受苦”的叙事。
住宫殿的人未必剥夺了他什么,他愤懑的对象并非具体的行为,而是“差距”本身。于是忍不住心生嫉恨,甚至怨怼社会。这种心理隐含了一个未经反思的前提,即结果必须绝对均等,简化了复杂的社会归因,继而断定“有贫富,即不公”。
说回俞敏洪南极信风波,其实新东方员工完全称得上一份体面的工作,根据某求职网站数据,新东方平均工资为¥10120/月。一个员工如果沉湎于“老板在南极,我却在加班”的失落而消极怠工,就更难抓住升职加薪的机会。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在《财富、贫困与政治》一书中阐述,落后群体是通过靠近、学习先进群体,提高生产率,创造更多价值来摆脱落后的,而憎恨先进群体完全无济于事,只会酿成悲剧。
所以,比较有必要,姿势更重要。

撰文 | 钱琪瑶
*本文为BOOK方物独家原创内容
未经BOOK方物授权不得转载,欢迎分享转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