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条例双刃剑:风景名胜区的文化脉络与国民权益将流向何方?
日前,国务院签署总理令,《风景名胜区条例》迎来关键修改,主管部门正式从住建系统划转至林草系统,这部法规的修改,又一次引发关于中国自然与文化遗产管理模式的反思与忧虑。

最新颁布的国务院令,对《风景名胜区条例》作出了引人注目的修改,直接改变了风景名胜区的“管家”——从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全面划转至林业和草原系统。
看似简单的部门调整,却牵动着全国244家国家级和近千家省市级风景名胜区的未来命运。
01 改革背景
此次条例修改的核心内容,是将风景名胜区的主管部门从住建部变更为国家林草局。这一变革源于2019年《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修改后的《风景名胜区条例》明确规定,风景名胜区的总体规划由国务院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审批,并会同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文物等有关部门审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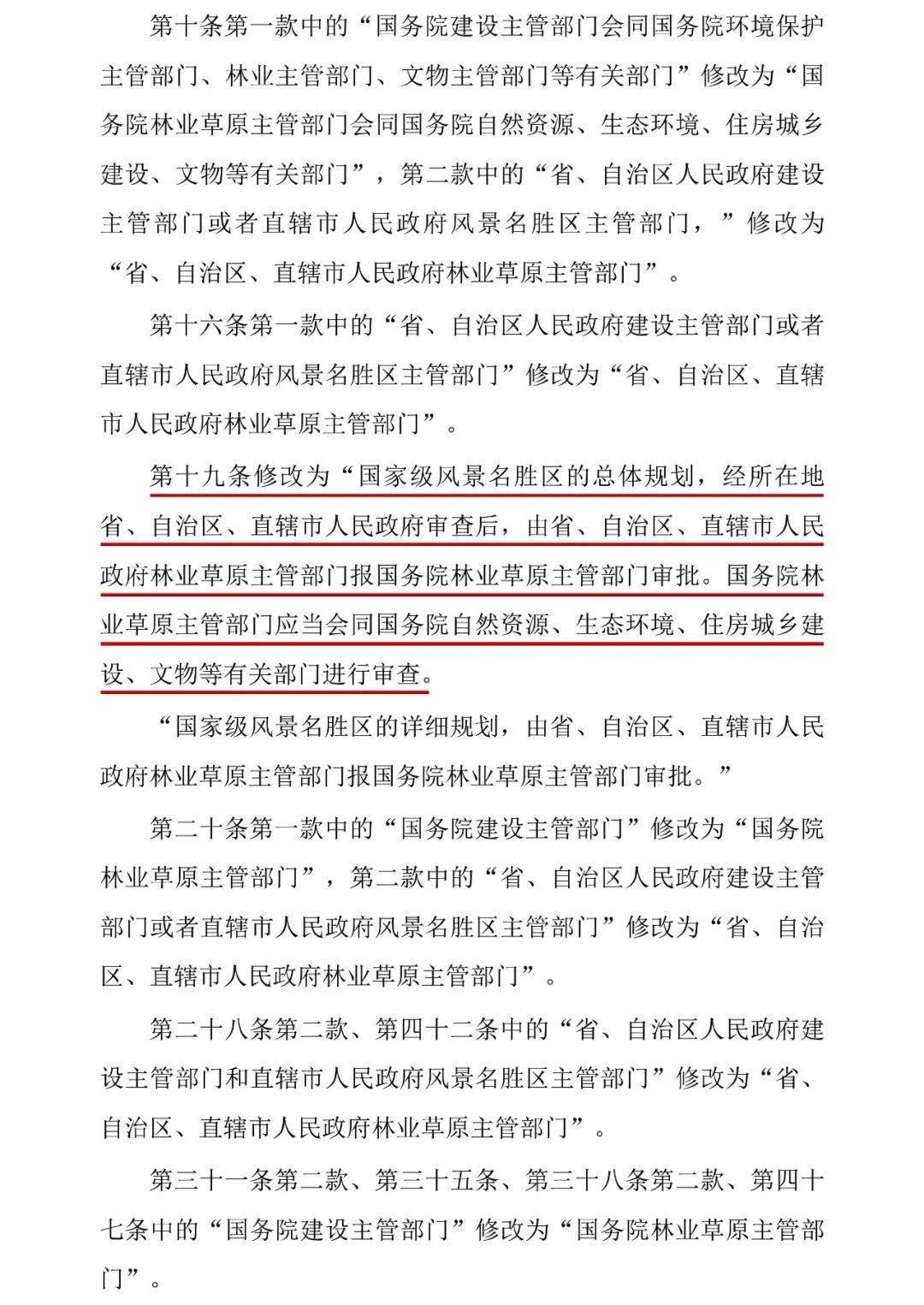
这一修改标志着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体制的重要转型,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性进步。从“建设开发”到“生态保护优先”的转变,符合全球自然保护的趋势。
但这一变革背后,隐藏着两个急需解答的问题。
02 文化属性之忧
风景名胜区的“名胜”二字,代表着深厚的文化沉积。从五岳的封禅文化到佛教四大名山的宗教传统,从西湖的文人雅集到黄山的山水画意,中国的风景名胜区从来不是纯粹的自然保护区。
以泰山为例,这座“五岳之首”不仅拥有独特的地质构造和生态系统,更承载着中国数千年的封禅祭祀文化、石刻艺术和古建筑群。

泰山上的岱庙、南天门、碧霞祠等古建筑群,与山势融为一体,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独特景观。

当主管部门从住建部转为林草局,管理思维随之转变。林业和草原系统的核心任务是生态保护与修复,特别是野生动物及其生境的保护,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显然不属于其专业领域。自然资源部门的专业优势在于森林资源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生态系统恢复。
但风景名胜区的灵魂不仅在于其自然景观,更在于其文化脉络。这些文化遗产需要专业的历史地理学者、考古文物专家、古建筑规划设计和民族文化研究者共同呵护。
新条例中确实规定了林业草原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文物部门审查风景名胜区的总体规划,但这能否确保文化属性不被生态保护的话语所淹没,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03 国民权益保障之困
新条例的另一个隐忧在于,规划审查过程中文化和旅游部的缺席。尽管文旅部在风景名胜区的旅游发展和公共服务方面负有重要职责,但在新条例规定的会同审查部门中,并未明确提及。特别担心国家公园法中那个非常不科学、不文化的“核心保护区禁止人为活动”的观念会逐步渗透到风景名胜区当中来:如果任由这样的趋势蔓延,中国人民对于风景名胜区的吸引物权就会受到严重的剥夺。
这一制度设计引发了对于国民游览权利保障的担忧。风景名胜区作为全民所有的公共资源,其核心价值之一就是为全国人民提供精神文化享受和公共游憩服务。
这涉及到一个基本权利问题——“吸引物权”,即公众对具有特殊吸引力的公共资源的享有权。如果规划过程中缺乏对旅游公共服务和大众游憩需求的专业考量,可能导致风景名胜区在保护的名义下,逐渐失去其公共属性。

部分自然保护地管理实践中已出现类似问题:为保护生态而严格限制游客数量、缩短开放时间甚至关闭部分区域,虽然从生态保护角度看是合理的,但也可能实质上限制了公众的享用权利。
04 潜在矛盾与应对之策
风景名胜区管理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如何在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资源保护与公共利用之间寻找平衡点。
国际经验提供了一些启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保护地管理分类体系中,明确区分了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和允许适度利用的保护地。
中国的风景名胜区更接近于“保护性景观”或“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类别,需要专门的管理策略。
有效的解决方案可能包括:建立多部门协同决策机制,确保文化、旅游部门的实质性参与;制定分类管理政策,对不同类型风景名胜区采取差异化管理措施。
最重要的是,管理目标应从“保护一个静态的物”转变为“监护一个动态发展的文化-自然过程”,在保护生态底线的同时,延续风景名胜区的文化生命力和公共属性。

05 变革的前景
新条例的实施效果将取决于具体执行中的制度设计。如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能够超越传统自然保护地管理模式,发展出一套适应风景名胜区独特属性的治理体系,这次改革可能成为我国自然文化遗产管理的里程碑。
反之,如果文化属性被生态保护话语所淹没,如果国民的游览权利在保护的名义下被不当限制,那么这次改革可能会偏离其初衷。
风景名胜区的未来不应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应是在保护与发展、自然与文化之间寻找精妙平衡的艺术。
改革就像是在古老的山径上开辟新路,既不能破坏原有的文化肌理,又要防止生态系统的脆弱平衡被打破。这条新路需要更多元的专业知识和更开放的公共参与,才能通向一个既能守护自然又能传承文化的未来。
作者 |吴必虎 DeepSeek
编辑 | 周晴
图源| 网络
